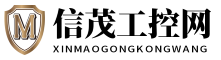富士康转型升级最大的象征意义,就是让中国制造业摆脱“代工”的命运,从制造商转向连锁经销商。
文字| 梁秋猛
2019年6月,也就是谷歌宣布华为手机无法运行GMS服务一个月后,央视《对话》制作了一档名为《数字时代的科技思考》的节目。 计算机专家倪光南、王健均为嘉宾。 当王健谈到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三大手机系统YunOS时,镜头转向倪光南,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。
倪呼吁PC时代的自治系统,王呼吁手机时代的自治系统。 遗憾的是,时代变了,霸主也变了,但我们缺乏操作系统的事实却从未改变。
在电动汽车呈现爆发趋势之际,另一位“大牛”也开始呼唤自动驾驶系统。 不过,它的身份有点特殊。 它就是从事代工行业40多年的富士康。
去年10月,富士康宣布了一种新架构,可以为各种类型和尺寸的电动汽车开发。 该开放平台被命名为MIH。 富士康表示,该平台将适用于任何制造商或品牌的车辆。
话虽如此,这个平台上的信息更多还是处于生产制造层面。 富士康尚未提及如何开发汽车行业的“操作系统”、如何支持汽车、如何构建生态系统。
但今年,富士康的步伐又开始加快。 与拜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后,又与吉利控股成立合资公司。 对于与吉利的合作,官方声明如下:“合资公司将为全球汽车及出行企业提供整车或零部件、智能控制系统、汽车生态系统以及汽车全产业链全流程服务。电动汽车。”
有趣的是,如果你在搜索软件上搜索“汽车行业的Android”,你会发现首页上只有两家公司,一家是富士康,一家是吉利。
微软Windows的崛起,与制造电脑的IBM、制造芯片的英特尔密不可分; 谷歌Android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。 这也为富士康与吉利的合作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
很多人嘲笑富士康“高估自己的能力”、“缺乏战略”、“像无头苍蝇”。 确实,与乘势5G、备受期待的华为鸿蒙相比,富士康的技术积累绝对是“相形见绌”。 但即便是靠代工为生的富士康也坐不住了。 这背后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——国内的应用生态中,几乎没有人的地盘。
1 从PC到手机,一座又一座城市失败
事实上,对于操作系统而言,中国市场并非没有燃过火。
20世纪90年代末,尚未被联想电脑解雇的倪光南就四处奔波,呼吁中国抓住开源系统Linux的机遇。 当时微软的反垄断案风头正劲,开源系统Linux成为了当时大家的选择。 开源系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原则免费使用和修改它们。
利用这套全球开放的代码,国产Linux才真正起飞,登上了舞台。
著名的Linux产品有Xteam、Blue Dot、ChinaSoft和Red Flag。
然而,虽然政府从系统到应用软件都无条件支持国产Linux,但尴尬的是地方部门可以用国产系统缴纳配额,却无法做生意,也没有资金入账。
后来,由于微软灵活运用策略,不仅部分订单半卖半送,还与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技术中心,甚至斥资数千万美元投资国内软件公司,最终改变政府采购政策。
国内电脑企业也纷纷涌向微软。 2006年,方正、清华同方等国内计算机企业访问美国,向微软下了总计17亿美元的订单。 虽然联想开发了自己的Linux系统,但仅仅提升了两年就让研发团队陷入了搁置。
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的电脑的用户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,安装盗版Windows。
至此,国内技术落后的Linux公司已经濒临崩溃。
在PC领域,国产操作系统已经节节败退。 在手机领域,又是一段耻辱的历史。
在苹果之前,智能手机系统以BlackBerry、Symbian、WindowCE等为主,这些系统的思想基本上是PC系统的延伸。 2005年,谷歌也瞄准了操作系统。 它直接收购了安卓(Android)公司,以减少蒙在鼓里的时间。
不过,直到iPhone的发布,整个行业才变得清晰起来,苦苦探索的智能手机也有了方向。
彼时,世界在手机操作系统方面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中国也派出了选手:2007年11月,中国移动探索与微软、谷歌合作研发。
背靠4亿用户,中国移动希望引领发展。 但显然微软和谷歌并不买账。 由此,中国移动与新成立的博斯通信联手,自主开发开放移动系统(简称OMS)。
但由于各合作手机厂商都有定制化需求,需要提供专门的团队支持,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。 结果OMS才推出一个版本,Android就已经更新了两三代了。 差距越来越大。 手机厂商和用户都相当不满,手机系统逐渐走向终结。
2010年,雷军通过更换界面、调整插件等方式“美化”了Android系统。 MIUI独特的风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一批手机厂商也开始效仿。 但这并不能代表多大的创新能力。
当然,也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人。 2010年,王健博士带领的阿里巴巴团队开发了有别于Android的YunOS,并吸引了手机厂商天语的橄榄枝。 两人先后合作发布了W700、大黄蜂等手机,但批评多于赞扬,只能遗憾分手。
至此,中国玩家已经从手机操作系统谢幕。
2 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,就永远是“贴牌”
作为苹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,富士康一定对操作系统的好处有着无尽的愿景。
据媒体报道,2019年,苹果在中国苹果专卖店的收入高达200亿美元,相当于5家富士康的利润。
事实上,即使不是“正经”的代工厂,中国市场,包括整个东亚地区,也正在重复着几乎“代工厂”的命运。
目前90%以上的智能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台式机都是东亚生产的,在电子元器件领域也占有绝对优势。 然而,这种优势并不能掩盖整个行业“互利发展”的弊病。
这是一个关于 DRAM 内存芯片行业的故事。
在台湾的双星中,其中一颗星指的是以代工起家的DRAM产业。 2008年,台湾出货量达到全球的1/4。 韩国三星掌门人李在镕看在眼里、心痛不已,于是决定前往台湾“考察学习”。
李在镕视察结束后,金融危机爆发。 三星召开内部高层会议,提出了名为“杀台”的计划。
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正如其名字一样雄心勃勃:首先摧毁台湾的DRAM存储芯片,然后摧毁富士康和台积电。 有台媒询问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对韩国“杀台”计划有何看法,郭台铭义正言辞地回应:如果真的来了,我会用关公的大刀砍回去。
这里的“大刀”指的是价格。
三星趁势,依托财阀背景,扩大生产,打价格战。 最终,台湾DRAM产业遭受重创,数万亿美元投资白费,台湾人均损失新台币5万元。
这个行业之所以脆弱,是因为DRAM行业产品标准化程度高,用户往往会选择谁便宜谁。 这导致企业不断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,以掌握最新技术并形成规模经济以摊销成本。 价格优势。 看似光鲜亮丽、尖端的电子行业,赚的是实实在在的辛苦钱。
产能霸权无法带来价格霸权,这是产业追逐者无法摆脱的陷阱之一。
郭台铭
反过来看行业龙头。
相关调查显示,一台电脑售价5000元,其中CPU价值1000-2000元,而英特尔可以赚取一半利润; 微软把边际成本接近0元的操作系统卖到1000多元。 也就是说,索尼、华硕、联想等品牌,杀得越狠,“英特尔+微软”就越稳。
移动时代,Android+Arm的新组合也正躺着看到来自三星、华为等品牌的激烈竞争。 据2018年调查显示,单台苹果手机利润高达151美元,而单台华为手机利润为15美元,OPPO和vivo分别为14美元和13美元,小米手机仅 2 美元。 利润如此微薄,不就相当于给安卓系统“代工”了吗?
“富士康”一方依然频频爆发价格战,但龙头企业却将精力集中在理论研发等领域,壁垒越来越高。
幸运的是,现在,有了新的赛道,那就是电动汽车。
有人预计,不久的将来,汽车行业将分为三类车企:主动转型的服务型车企,以用户触点为主的服务型车企将主导终端市场; 代工型车企,失去用户触点的企业,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面临淘汰或者成为代工厂; 新的代工厂,行业外的第三类玩家也将积极出击,积极为代工厂寻求新的角色。
富士康应该离不开新代工厂的作用。 不过,在电动汽车赛道上,富士康可能仍面临无穷无尽的追赶者,这将导致利润不断减少。 即使通过最残酷的战斗,也不可能消灭所有对手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富士康做出了大胆的声明——“成为汽车领域的谷歌Android”。 在电动汽车新赛道上,它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。
在PC端和手机端的两场较量中,中国这个大国已经两次惨败。 在电动汽车的争夺战中,富士康作为最边缘的“整车厂”,已经不能置身事外了。
当然,从目前的业绩来看,富士康在软件业务上的表现并不是很亮眼。 有人透露,工业富联的云计算业务仍以硬件代工为主,软件业务相对较小,这使得公司云计算业务的毛利率仅维持在4.48%。 这意味着,虽然被工业互联网、云计算覆盖,但富士康在该领域的业务仍以代工为主。
但无论怎样,难能可贵的是富士康有改变的想法。 这个“代工巨头”的翻身,代表着中国整个制造业的迫切转型。 让中国制造业摆脱“代工”命运,从制造商转变为链条制造商,是富士康转型升级背后最大的象征意义。
【峰会论坛】【浩浩下午茶】